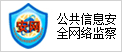核心提示:
1998年以后,隨著中國經(jīng)濟短缺格局的結束,從賣方市場轉(zhuǎn)變?yōu)橘I方市場,物價走勢也有了新的變化。在此背景下,一些人簡單搬用西方經(jīng)濟學中的“通脹”或“通縮”概念來解釋中國經(jīng)濟運行中的物價變動。如果“通脹”或“通縮”只是用于描述物價走勢的一組概念,本無可厚非,但常常發(fā)生的是,人們習慣地將其與貨幣政策相聯(lián)系,似乎CPI的變動總是由對應的貨幣政策引致的,因此,在落實到政策主張時,使用這組概念的人總是在邏輯上推演出了相應的貨幣政策調(diào)整。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將CPI變動簡單地歸結為貨幣政策效應的思維,甚至影響到了貨幣政策決策乃至經(jīng)濟決策層面。
1998年以來物價變動與貨幣政策無必然關系
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的物價變動始終沒有停止,既有物價上行的時期,也有物價下落的走勢,但總趨勢是上行的。細究各次物價變動的成因,不僅不盡相同,而且相當復雜。
從物價上行看,主要有5種情形:第一,價格向價值回歸過程中的物價上行。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中國有著相當多基本生活用品處于購銷倒掛狀態(tài),采用財政補貼方式維系它們的生產(chǎn)銷售。在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改革過程中,一項重要舉措就是變“暗補”為“明補”,這自然引致物價上漲。第二,資源貨幣化過程中的物價上行。在中國傳統(tǒng)體制下,諸如土地、技術等資源是沒有價格的。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這些資源的貨幣化進程大大加快,利用這些資源的各種費用理應計入企業(yè)生產(chǎn)銷售的財務成本,由此,必然推進商品價格的上行。第三,由商品供不應求引致的物價上行。這是一般經(jīng)濟學原理,無須贅述。第四,由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上漲引致的國內(nèi)物價上行。這種物價上行的程度,既取決于國內(nèi)對相關商品的自給能力和程度,也取決于相關商品的對外開放程度。 08年上半年,國際市場上大米等糧價大幅上漲(上漲了2倍左右),中國國內(nèi)市場中大米等糧食價格并沒有隨之同幅度上行,一方面是因為國產(chǎn)大米等糧食基本上能夠滿足國內(nèi)消費和生產(chǎn)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國產(chǎn)大米等糧食沒有大幅進入國際市場循環(huán)。與此不同,同期國際市場中的石油等資源類產(chǎn)品價格大幅上漲,對中國就有比較明顯的影響。第五,由貨幣發(fā)行過多引致的物價上漲。這就是“通脹”。從這5種情形來看,前3種不是由貨幣政策過松引致的,貨幣政策對它們基本無能為力。第4種雖然可以利用匯價機制予以弱化,但面對國際市場大宗商品交易中價格上漲,對一國的外匯儲備量而言,貨幣政策可發(fā)揮效能的余地相當有限。只有第5種屬于“通脹”,貨幣政策調(diào)整有著明顯的效應。
從物價下落看,主要情形有四:第一,由政府財政機制引致的物價下落。其中,既包括運用財政補貼降低價格,也包括通過降低稅收來降低商品價格。第二,由政府行政機制引致的物價下落。這類情形比較復雜,其中,既包括諸如設立蔬菜等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綠色通道,取消相應的過路費,以降低這些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價格,也包括動用國家儲備來穩(wěn)定市場乃至打壓對應商品的市場價格,還包括政府部門直接出臺降價政策。第三,由商品供過于求引致的物價下落。這在單種或少數(shù)幾種商品的場合比較容易理解,但在多數(shù)商品近乎同期發(fā)生供過于求的場合,一些人就陷入了迷茫狀態(tài)。第四,由貨幣發(fā)行過少引致的物價下落。這種情形被稱為“通縮”。從這4種情形看,前3種與貨幣政策基本無關,貨幣政策緊縮對它們沒有什么效能,只有第4種是由貨幣供給量過少引致的,由此,適當放松貨幣政策將有明顯效應。
在中國,1998年以后10多年的CPI走勢和貨幣供應量走勢,以CPI增長率變動為據(jù),從中可以看到幾個重要時期:(1)1998-2002年間的物價負增長或低增長時期;(2)2003-2004年間的物價高增長或正增長時期;(3)2007-2008年間的物價高增長時期;4)2009年前6個月的物價負增長時期。
首先,看1998-2002年間的物價負增長,如果就1998和1999年的CPI增長率為-0.8%和-1.4%而言,似乎可以得出通縮的判斷。但如果聯(lián)系到貨幣供應量來看,判斷就不同了。從M2看,1998-1999的兩年間,M2的增長率分別為14.8%和14.7%,明顯高于CPI為0.4的2000年(這年的M2增長率為12.3%);從M1看,雖然1998年的M1增長率從1997年的22.1%下落到11.9%,由此,似乎可以為CPI從2.8%降低到-0.8%找到一些根據(jù),但1999年M1又上升到17.7%(而CPI繼續(xù)降低到-1.4%),恐怕就很難再用這種根據(jù)來解釋了。因此,這一時期的物價下落與貨幣供應量多少無關。其次,看2003-2004年間的物價高增長或正增長,但同期M2和M1的增長率分別從19.6%和18.7%降低到14.7%和13.6%,這恐怕難以直接說明物價上行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了。再次,看2007-2008年間的物價高增長,2007年物價上漲率達到4.8%、2008年更是達到了5.9%,但同時M2的增長率從2005年的17.6%下落到2007年16.7%,2008年M2雖達到了17.79%,但M1的增長率僅為8.98%。因此,將這一時期的物價上漲歸咎于貨幣供應過于寬松,是無法得到數(shù)據(jù)支持的。最后,看2009年1-6月的物價負增長,CPI增長率為-1.7%,而同期的M2和M1增長率高達28.46%和24.79%,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高點,更是與CPI負增長不對應。
要將1998年以來的中國物價變動界定為“通脹”或“通縮”,就必須有效證明這些物價變動與貨幣供應量松緊之間的函數(shù)關系,但從四個時期的簡要分析中可見,這種函數(shù)關系是無法確立的。準確地說,這些年只存在物價變動,不存在“通脹”或“通縮”。
以“通脹”或“通縮”表述物價變動弊端多
“通脹”和“通縮”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著確定的含義和政策主張,在上述 四個時期中,以“通脹”和“通縮”來表述物價變動,有著一系列嚴重的負面效應。
從理論層面看,這種表述處于邏輯混亂且自相矛盾之中。首先,1998年的物價下落是由于絕大多數(shù)產(chǎn)品都發(fā)生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從而中國經(jīng)濟實現(xiàn)了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zhuǎn)變。在商品供過于求的條件下,降價銷售成為廠商在市場營銷中的第一選擇,由此,自然引致物價下降。值得特別強調(diào)的是,這種買方市場格局的形成是中國改革開放、推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目標。曾記得,在1987年左右,有人試圖證明社會主義經(jīng)濟只能在短缺中運行和發(fā)展,但經(jīng)過中國人民的努力,中國終于甩掉了“短缺經(jīng)濟”帽子,這是何等偉大的成就。然而,強調(diào)要“治理通縮”的主張,卻試圖改變由買方市場所引致的物價下降,由此,提出了一個邏輯上的問題,這種“治理通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再回到賣方市場?其次,2003年8月隨著夏糧收購的完成,中國進入了連續(xù)第四個糧食減收的年份,由此,在供不應求的條件下糧食價格上行,這引致了物價向正增長方向轉(zhuǎn)變。對前期主張“治理通縮”的人來說,這應是一個好消息(經(jīng)過5年的呼吁,“通縮”終于結束了,所以,應當慶賀),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隨即提出了要“防止通脹”的主張,并于2004年明確提出了要“治理通脹”的主張。2004年,在糧價上行和財政補貼的雙重作用下,農(nóng)民的種糧積極性大幅提高,使得當年糧食大幅增收,由此,CPI增長率在2004年9月達到5.3%以后扭頭下行,到2005年1月已落到1.9%。這作為“治理通脹”的結果應當慶賀吧,但馬上又轉(zhuǎn)向提出了要“防止通縮”的主張(同時,也有一些人強調(diào)要繼續(xù)“治理通脹”,并以當時的PPI明顯高于CPI為依據(jù),認為PPI的上漲將傳遞到CPI),由此,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是否經(jīng)濟運行中只存在著這樣一種情形——要么“通脹”、要么“通縮”,從而,學者們需要不斷地在二者之間折騰?再次,2007-2008年間,隨著豬肉及肉制品、糧食和食用油等食品類價格的上揚(其中,豬肉及肉制品的價格上行主要由國內(nèi)因素引致,糧食和食用油價格上行主要受國際市場因素影響),中國又一次進入了CPI高漲期,由此,“治理通脹”的呼聲再次鵲起。隨著各項刺激養(yǎng)豬政策的落實和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的回落,進入2009年以后,物價大幅下行,7月份CPI為-1.8%,這應當為“治理通脹”慶賀了吧,可是一些人又再次轉(zhuǎn)向,當即提出了“治理通縮”的政策主張。在2008年的物價上漲中,并非各種消費品的價格普遍上行,在“食品”、“煙酒及用品”、“家庭設備及用品”、“醫(yī)療保健用品”和“居住”等價格上漲的同時,“衣著”、“交通和通訊工具”及“娛樂教育文化用品”等的價格處于持續(xù)降低走勢。其中,漲幅最大的是“食品”,2008年1-8月的漲幅都在兩位數(shù)。與此相比,2009年2月以后,“食品”價格呈負增長走勢(在實際生活中,豬肉及肉制品、糧食和食用油等絕對價格下降了),在此背景下,提出“治理通貨緊縮”的含義是什么呢?如果這些食品的價格不該下降,那么,為什么在2008年同期需要疾呼“治理通貨膨脹”?如果這些食品的價格應該下降,那么,提出“治理通貨緊縮”的意圖又是什么?真是不知所云。1998年以來,理論界一些人在“通脹”和“通縮”上的反復無常、莫衷一是,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面對物價變動,能否簡單地套用“通脹”或“通縮”的理論思維?換句話說,是否存在既不需要“治理通縮”也不需要“治理通脹”的物價狀態(tài)?
從1997-2007的11年間CPI分類指數(shù)的變化走勢,從中可以看到,食品類價格指數(shù)有兩次大幅上行,即2004年的9.9%和2007年的12.3%,它們是引致對應年份CPI高漲的主要成因。從具體情況看,2004年主要是糧食價格上漲,2007年以后主要是豬肉及肉制品價格上漲,這些都涉及到農(nóng)產(chǎn)品和農(nóng)民的利益。農(nóng)業(yè)是國民經(jīng)濟的基礎。在中國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也存在著支持“三農(nóng)”發(fā)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繁重而艱巨的任務,由此,提高農(nóng)民收入,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應當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予以認真解決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而且有著繼續(xù)擴大的趨勢。究其原因,農(nóng)產(chǎn)品的價值構成與工業(yè)品不同是一個主要方面。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商品價格應由C+V+M三部分構成。中國的工業(yè)品價值的確由C+V+M構成,但大部分農(nóng)產(chǎn)品卻只由C+V構成。由于在農(nóng)產(chǎn)品中缺乏M,所以,資本進入農(nóng)業(yè)的傾向大大減弱,金融服務于農(nóng)業(yè)的程度也明顯不足。盡管如此,對農(nóng)民來說,只要能夠保證V的獲得,也還有種糧養(yǎng)豬的積極性。但是,糧價在1996年達到了高點(84.23元/100斤)以后就一路下落,到2000年降至谷底(49.39元)/100斤,跌幅深達41.36%。在此背景下,隨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的價格上漲,農(nóng)產(chǎn)品中C部分加大,V的獲得更加缺乏保障,在此背景下,盡管各地方政府采取了種種措施力保糧食生產(chǎn),但糧食種植面積還是從1998年的113787公頃減少到2003年的99410公頃(降幅達到12.63%),由此,引致了糧食的年產(chǎn)量從1998年的51229.5萬噸減少到2003年的37428.7萬噸(降幅達到26.94%)。這是2003年底至2004年物價大幅上漲的基本成因。支持這一物價上漲,意味著讓農(nóng)民多少能夠從糧食及其他農(nóng)產(chǎn)品中獲得一些收入,以維系V的應有水平,激勵他們的種糧積極性。但所謂的“治理通脹”則要求抑制糧食及其他農(nóng)產(chǎn)品的價格上漲,使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繼續(xù)處于受挫狀態(tài)。顯然,從實踐面情況看,此時提出“治理通脹”是不合時宜的。實踐中的政策選擇是,在放棄動用國家儲備糧打壓糧價、讓市場機制推進糧價回升的同時,財政部門對種糧農(nóng)民進行了按照耕種面積的“直補”,從而刺激了農(nóng)民種糧積極性,使得2004年扭轉(zhuǎn)了持續(xù)4年的糧食減收走勢,穩(wěn)定了糧食價格,促使CPI增長率下行。
2007年初發(fā)生了新一輪的物價高漲,它主要由豬肉及肉制品所引致。與2006年相比,2007年肉豬出欄減少了4699萬頭(即下降了7.68%),豬肉產(chǎn)量減少了362.7萬噸(即下降了7.80%)。豬肉產(chǎn)量減少的成因主要在于養(yǎng)豬成本的上升,其中包括飼料價格升高、防疫(如藍耳病等)成本提高和規(guī)模化養(yǎng)豬的設施成本上升等。由于原先豬肉的價格水平無力消化這些成本上升引致的養(yǎng)豬虧損,所以,一些農(nóng)民不愿繼續(xù)養(yǎng)豬,由此,導致豬肉供不應求,豬肉價格隨之走高并推動了CPI上行。但一些學者無視這一現(xiàn)實現(xiàn)象,再次提出了“治理通脹”的政策主張,好在實際操作中,有關政府部門采取了財政補貼,其中包括無償防治藍耳病、給每只母豬以一定數(shù)額的財政資助等,由此,在2008年下半年,生豬存欄量大幅增加,生豬價格從10元/斤左右直線下落到6元/斤左右。豬肉及肉制品價格的下落,促成了CPI下行。2008年1-8月,食品類價格指數(shù)上漲率均在2位數(shù)(其中最高的是4月份22.1%),但到2009年2月以后,隨著豬肉價格絕對水平的降低,CPI也就呈負增長走勢。在此背景下,再次提出“治理通貨緊縮”的實踐含義是什么?是預期讓豬肉及肉制品再陷入短缺境地從而價格繼續(xù)走高,還是預期使食品類中的其他產(chǎn)品(如糧食等)價格走高,以便在CPI上行中又一次炒作“治理通脹”?
從實踐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論是“治理通脹”還是“治理通縮”都無助于解決1998年以來中國實踐中發(fā)生的CPI增長率變動,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針對物價變動的具體成因,分別選擇不同的政策措施。
最后,從政策層面看,既然將物價變動簡單地定義為貨幣政策松緊的現(xiàn)象,既然央行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是保持幣值穩(wěn)定(而物價變動意味著幣值變動),所以,在物價變動中,主張調(diào)整貨幣政策松緊程度的呼聲不絕于耳。從歷史線索看,(1)在所謂“通縮”的背景下,1996-2002的7年間,央行先后8次下調(diào)了存貸款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下落到1.98%、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落到5.31%,其力度不能說不大。下調(diào)存款利率的一個重要意圖是,希望城鄉(xiāng)居民少存款多消費,但結果是,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95年底的2.97萬億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8.69萬億元(原先每年新增儲蓄存款6000億元左右,但2000年之后,每年新增儲蓄存款在1萬億元左右),另一方面,這段時間內(nèi)的CPI走勢并沒有發(fā)生實質(zhì)性改變。(2)在2003-2004年的所謂“治理通貨膨脹”過程中,央行于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分別兩次提高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共1.5個百分點)、于2004年10月提高存貸款利率(1年期存貸款利率分別上調(diào)0.27個百分點),但這些措施對緩解糧食產(chǎn)量的下降并無多少正面效應,相反的,它引發(fā)了其他一系列問題的產(chǎn)生。 2004年5月以后,民營經(jīng)濟發(fā)展陷入困難境地、證券公司大幅虧損(以致10月份以后,一大批證券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由此,拉開了證券公司破產(chǎn)整頓的序幕)等等,與此時緊縮的貨幣政策不無關系。(3)2007-2008年間CPI高增長期間,央行先后16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9%上升到17.5%)、6次提高存貸款利率,但并沒有因此遏制住CPI不斷上行的勢頭;2008年9月以后的3個多月時間內(nèi),連續(xù)4次下調(diào)法定存款準備金率、5次下調(diào)存貸款利率(使1年期存款利率回到了2004年10月底的水平,1年期貸款利率回到了2002年2月的水平),但CPI下行的走勢并沒有因此而改變。在這些調(diào)整中,一系列負面效應隨之而來:其一,對養(yǎng)豬戶而言,提高利率無助于豬肉及肉制品價格進一步上升,但貸款利率的上升將使養(yǎng)豬專業(yè)戶的成本(包括由貸款利率上行引致的飼料價格上升)增加,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財政補貼的效能。其二,在不斷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過程中,對中小存貸款金融機構來說,由于缺乏外匯資產(chǎn),只能上繳人民幣資金,由此,陷入可貸資金緊張狀態(tài),這進一步引致了中小企業(yè)貸款的縮減和貸款利率上行,加重了中小企業(yè)融資的困難。其三,干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實施。其四,影響了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進程。2004年10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fā)布了《關于調(diào)整人民幣基準利率的通知》,強調(diào)貸款利率以基準利率為下線,上限全部放開,由各家存貸款金融機構“根據(jù)自身經(jīng)營狀況、資金成本和企業(yè)風險程度等因素合理確定存貸款利率”,這意味著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將邁出實質(zhì)性步伐。在商業(yè)銀行體系內(nèi)資金過剩背景下,貸款利率本來有著下行要求(至少說,持續(xù)上行是相當困難的),但在“治理通脹”過程中,強制性地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由此,影響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的應有進程。
中國有句俗語:殺雞焉用牛刀。1998年以來中國物價變動的具體成因在各個時期是不一樣的,理應選擇“具體問題具體解決”的研討思路和政策取向,但將這些物價變動冠之以“通脹”或“通縮”并由此引致運用貨幣政策,以需求總量政策來解決某種農(nóng)產(chǎn)品供不應求(或提高農(nóng)民生產(chǎn)這種農(nóng)產(chǎn)品的積極性)問題,只怕是“雞未能殺死”卻“傷了自己”。
走出“通脹”或“通縮”的思維誤區(qū)
物價走勢是判斷宏觀經(jīng)濟走勢的一個重要指標。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經(jīng)濟運行走勢,不僅對中國的未來發(fā)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球經(jīng)濟的復蘇也是舉足輕重的。2009年1-7月,中國經(jīng)濟運行撲朔迷離,新增貸款規(guī)模、固定資產(chǎn)投資規(guī)模等創(chuàng)下了歷史新高,工業(yè)增加值、制造業(yè)采購經(jīng)理指數(shù)(PMI)和發(fā)電量緩慢回升,股價、房價上行趨勢明顯,物價、出口增長率繼續(xù)維持負增長,GDP在第二季度達到7.9%的基礎上還將繼續(xù)上行。從2009年的后期看,新增貸款規(guī)模、固定資產(chǎn)投資規(guī)模的全年高增長已成定局,工業(yè)增加值、制造業(yè)采購經(jīng)理指數(shù)(PMI)、發(fā)電量、股價、房價等將繼續(xù)上行,物價上漲率、出口增長率可能轉(zhuǎn)負為正,第四季度的GDP可能達到10%左右,照此慣性運行,2010年上半年的中國經(jīng)濟將在高位運行,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經(jīng)濟是否又進入了一個類似于2007年的“過熱”區(qū)間?與此對應,是否需要再來一次宏觀經(jīng)濟緊縮? 在做這一判斷中,對物價變動狀況的認定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雖然在新增貸款規(guī)模和固定資產(chǎn)投資規(guī)模等高增長而CPI負增長的背景下,有人強調(diào)要“治理通縮”,有人則強調(diào)要“防止通脹”,這些爭論還難有定數(shù),可是一旦CPI轉(zhuǎn)向正增長,“治理通脹”的呼聲就將占據(jù)上風。
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是,在產(chǎn)能過剩比較嚴重的格局中,中國目前并不具備通脹的現(xiàn)實條件,同時,按照2008年物價上漲的翹尾因素分析,2009年的物價應當呈負增長走勢,但是,在《政府工作報告》所列的2009年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中,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被界定在4%左右。如此高的CPI目標,是計算缺乏科學性,還是已有一些價格調(diào)整的預案?從該報告的“2009年主要任務”中可以看到:“推進資源性產(chǎn)品價格改革。繼續(xù)深化電價改革,逐步完善上網(wǎng)電價、輸配電價和銷售電價形成機制,適時理順煤電價格關系。積極推進水價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農(nóng)業(yè)用水價格,完善水資源費征收管理體制。加快建立健全礦產(chǎn)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tài)補償機制,積極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這意味著,在2009年間,隨著國民經(jīng)濟增長態(tài)勢轉(zhuǎn)好,各項經(jīng)濟指標比較理想時,可能啟動水、電、燃氣等方面的價格改革,這將推動CPI呈正增長走勢。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由價格調(diào)整所引致的CPI正增長是否也屬“通脹”,需要用從緊的貨幣政策措施予以抑制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則不僅與政府的價格調(diào)整政策相矛盾,而且將引致更為嚴重的宏觀經(jīng)濟緊縮后果。
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和今后的進一步發(fā)展中可以看到,物價變動是由多種成因所致,其中大多數(shù)與貨幣政策的松緊基本無關,因此,既不能用“通脹”或“通縮”冠之,也不應對CPI變動簡單地采取對應的貨幣政策。只有那些因貨幣發(fā)行過多引致的物價上漲或因貨幣發(fā)行過少引致的物價下降,才可冠之以“通脹”或“通縮”,選擇對應的貨幣政策實施影響。
必須認識到一個重要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在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中,農(nóng)產(chǎn)品、資源類產(chǎn)品(包括礦產(chǎn)品、水、電和燃氣等)的價格上行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趨勢。這既由資源的稀缺性所決定,也由這些產(chǎn)品生產(chǎn)的成本(包括環(huán)保成本)上升所決定。在此背景下,由這些產(chǎn)品價格上行所引致的物價上漲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鑒于中國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要真正維護農(nóng)民利益、推進“三農(nóng)”發(fā)展、激勵資本向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的上漲也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宏觀調(diào)控的目標不在于抑制這些產(chǎn)品的價格上漲(從而抑制由此引致的CPI上行),而在于熨平這種價格上漲走勢,以防價格上漲過快而影響到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從這個角度上看,問題不在于“治理”,而在于“熨平”。毫無疑問,在“熨平”這些產(chǎn)品價格上漲過程中,還需運用財政政策,在一定時期內(nèi)該補貼的還要補貼,但總的取向不應是“補貼”;應當讓農(nóng)民獲得按照市場機制所能夠獲得的收入,在此基礎上,再討論財政補貼問題。否則,本末倒置,將引致更加嚴重的負面后果。
面對由貨幣發(fā)行量引致的物價上漲,貨幣政策的松緊確有其功效。但面對不是由貨幣發(fā)行量引致的物價上漲,貨幣政策的松緊非但沒有功效而且有著諸多負面效應。由此來看,將貨幣政策目標界定在“保持貨幣幣值的穩(wěn)定”上是值得重新探討的。其一,貨幣政策沒有在任何物價變動條件下都保持幣值穩(wěn)定的功能,因此,做不到、也達不到這一目標。其二,將這一目標界定為央行工作的主要目標,容易使央行在面對物價變動中處于被動境地,不得不頻繁地出臺相關貨幣政策調(diào)整措施(以擺脫被動處境),而這些貨幣政策舉措可能不僅無的放矢,而且將引致不良后果。其三,央行雖是貨幣政策的調(diào)控主體,但也是維護金融運行穩(wěn)定的主要部門。“保持貨幣幣值的穩(wěn)定”主要目的還在于維護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穩(wěn)定。在防范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再度發(fā)生過程中,西方主要國家已將維護金融穩(wěn)定提高到至少不低于貨幣政策的程度。在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金融穩(wěn)定的重要性也將日益凸顯,為此,與其將央行的主要工作目標界定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wěn)定”,不如將其界定為“保持金融運行秩序的穩(wěn)定”。這也有利于避免“一旦CPI發(fā)生變動,就找央行(或貨幣政策)”的傾向繼續(xù)發(fā)生。
CPI漲跌和物價變動并不對等,其中一個重要差別在于CPI中各種產(chǎn)品價格的權重設置。在中國的CPI中,食品類所占權重達到1/3,這在推進溫飽型小康過程中是合適的。但如今,溫飽型小康已經(jīng)基本實現(xiàn),在推進全面小康過程中繼續(xù)采取這種權重計算方法,就容易產(chǎn)生負面影響。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是,一旦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上漲,CPI隨之反應,而根據(jù)“通脹”思維所采取的貨幣政策直接要求抑制農(nóng)產(chǎn)品的價格上行。這不利于維護農(nóng)民的利益,也不利于理順價格體系。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是指各種物價(主要是工業(yè)制成品)近乎普遍地持續(xù)(一般以6個月以上為度量標準)上漲或下跌的走勢。據(jù)此,CPI的權重構成調(diào)整可以選擇兩種方法:一是計算核心CPI,以此為度量是否通脹或通縮的指標。在核心CPI中,不列入食品類,由此,它只反映工業(yè)制成品的價格變動趨勢,更緊密地反映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經(jīng)濟運行態(tài)勢。二是降低食品類在CPI中的權重,從目前的1/3降低到與美國、印度等相近的水平(即10%左右),以減輕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變動對CPI的影響程度。兩種方法中,前者為好;當然,也可兩種方法都選用,但以前一種方法為主。
1998年以來物價變動與貨幣政策無必然關系
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的物價變動始終沒有停止,既有物價上行的時期,也有物價下落的走勢,但總趨勢是上行的。細究各次物價變動的成因,不僅不盡相同,而且相當復雜。
從物價上行看,主要有5種情形:第一,價格向價值回歸過程中的物價上行。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中國有著相當多基本生活用品處于購銷倒掛狀態(tài),采用財政補貼方式維系它們的生產(chǎn)銷售。在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改革過程中,一項重要舉措就是變“暗補”為“明補”,這自然引致物價上漲。第二,資源貨幣化過程中的物價上行。在中國傳統(tǒng)體制下,諸如土地、技術等資源是沒有價格的。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這些資源的貨幣化進程大大加快,利用這些資源的各種費用理應計入企業(yè)生產(chǎn)銷售的財務成本,由此,必然推進商品價格的上行。第三,由商品供不應求引致的物價上行。這是一般經(jīng)濟學原理,無須贅述。第四,由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上漲引致的國內(nèi)物價上行。這種物價上行的程度,既取決于國內(nèi)對相關商品的自給能力和程度,也取決于相關商品的對外開放程度。 08年上半年,國際市場上大米等糧價大幅上漲(上漲了2倍左右),中國國內(nèi)市場中大米等糧食價格并沒有隨之同幅度上行,一方面是因為國產(chǎn)大米等糧食基本上能夠滿足國內(nèi)消費和生產(chǎn)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國產(chǎn)大米等糧食沒有大幅進入國際市場循環(huán)。與此不同,同期國際市場中的石油等資源類產(chǎn)品價格大幅上漲,對中國就有比較明顯的影響。第五,由貨幣發(fā)行過多引致的物價上漲。這就是“通脹”。從這5種情形來看,前3種不是由貨幣政策過松引致的,貨幣政策對它們基本無能為力。第4種雖然可以利用匯價機制予以弱化,但面對國際市場大宗商品交易中價格上漲,對一國的外匯儲備量而言,貨幣政策可發(fā)揮效能的余地相當有限。只有第5種屬于“通脹”,貨幣政策調(diào)整有著明顯的效應。
從物價下落看,主要情形有四:第一,由政府財政機制引致的物價下落。其中,既包括運用財政補貼降低價格,也包括通過降低稅收來降低商品價格。第二,由政府行政機制引致的物價下落。這類情形比較復雜,其中,既包括諸如設立蔬菜等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綠色通道,取消相應的過路費,以降低這些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價格,也包括動用國家儲備來穩(wěn)定市場乃至打壓對應商品的市場價格,還包括政府部門直接出臺降價政策。第三,由商品供過于求引致的物價下落。這在單種或少數(shù)幾種商品的場合比較容易理解,但在多數(shù)商品近乎同期發(fā)生供過于求的場合,一些人就陷入了迷茫狀態(tài)。第四,由貨幣發(fā)行過少引致的物價下落。這種情形被稱為“通縮”。從這4種情形看,前3種與貨幣政策基本無關,貨幣政策緊縮對它們沒有什么效能,只有第4種是由貨幣供給量過少引致的,由此,適當放松貨幣政策將有明顯效應。
在中國,1998年以后10多年的CPI走勢和貨幣供應量走勢,以CPI增長率變動為據(jù),從中可以看到幾個重要時期:(1)1998-2002年間的物價負增長或低增長時期;(2)2003-2004年間的物價高增長或正增長時期;(3)2007-2008年間的物價高增長時期;4)2009年前6個月的物價負增長時期。
首先,看1998-2002年間的物價負增長,如果就1998和1999年的CPI增長率為-0.8%和-1.4%而言,似乎可以得出通縮的判斷。但如果聯(lián)系到貨幣供應量來看,判斷就不同了。從M2看,1998-1999的兩年間,M2的增長率分別為14.8%和14.7%,明顯高于CPI為0.4的2000年(這年的M2增長率為12.3%);從M1看,雖然1998年的M1增長率從1997年的22.1%下落到11.9%,由此,似乎可以為CPI從2.8%降低到-0.8%找到一些根據(jù),但1999年M1又上升到17.7%(而CPI繼續(xù)降低到-1.4%),恐怕就很難再用這種根據(jù)來解釋了。因此,這一時期的物價下落與貨幣供應量多少無關。其次,看2003-2004年間的物價高增長或正增長,但同期M2和M1的增長率分別從19.6%和18.7%降低到14.7%和13.6%,這恐怕難以直接說明物價上行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了。再次,看2007-2008年間的物價高增長,2007年物價上漲率達到4.8%、2008年更是達到了5.9%,但同時M2的增長率從2005年的17.6%下落到2007年16.7%,2008年M2雖達到了17.79%,但M1的增長率僅為8.98%。因此,將這一時期的物價上漲歸咎于貨幣供應過于寬松,是無法得到數(shù)據(jù)支持的。最后,看2009年1-6月的物價負增長,CPI增長率為-1.7%,而同期的M2和M1增長率高達28.46%和24.79%,創(chuàng)造了歷史的高點,更是與CPI負增長不對應。
要將1998年以來的中國物價變動界定為“通脹”或“通縮”,就必須有效證明這些物價變動與貨幣供應量松緊之間的函數(shù)關系,但從四個時期的簡要分析中可見,這種函數(shù)關系是無法確立的。準確地說,這些年只存在物價變動,不存在“通脹”或“通縮”。
以“通脹”或“通縮”表述物價變動弊端多
“通脹”和“通縮”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著確定的含義和政策主張,在上述 四個時期中,以“通脹”和“通縮”來表述物價變動,有著一系列嚴重的負面效應。
從理論層面看,這種表述處于邏輯混亂且自相矛盾之中。首先,1998年的物價下落是由于絕大多數(shù)產(chǎn)品都發(fā)生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從而中國經(jīng)濟實現(xiàn)了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zhuǎn)變。在商品供過于求的條件下,降價銷售成為廠商在市場營銷中的第一選擇,由此,自然引致物價下降。值得特別強調(diào)的是,這種買方市場格局的形成是中國改革開放、推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目標。曾記得,在1987年左右,有人試圖證明社會主義經(jīng)濟只能在短缺中運行和發(fā)展,但經(jīng)過中國人民的努力,中國終于甩掉了“短缺經(jīng)濟”帽子,這是何等偉大的成就。然而,強調(diào)要“治理通縮”的主張,卻試圖改變由買方市場所引致的物價下降,由此,提出了一個邏輯上的問題,這種“治理通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再回到賣方市場?其次,2003年8月隨著夏糧收購的完成,中國進入了連續(xù)第四個糧食減收的年份,由此,在供不應求的條件下糧食價格上行,這引致了物價向正增長方向轉(zhuǎn)變。對前期主張“治理通縮”的人來說,這應是一個好消息(經(jīng)過5年的呼吁,“通縮”終于結束了,所以,應當慶賀),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隨即提出了要“防止通脹”的主張,并于2004年明確提出了要“治理通脹”的主張。2004年,在糧價上行和財政補貼的雙重作用下,農(nóng)民的種糧積極性大幅提高,使得當年糧食大幅增收,由此,CPI增長率在2004年9月達到5.3%以后扭頭下行,到2005年1月已落到1.9%。這作為“治理通脹”的結果應當慶賀吧,但馬上又轉(zhuǎn)向提出了要“防止通縮”的主張(同時,也有一些人強調(diào)要繼續(xù)“治理通脹”,并以當時的PPI明顯高于CPI為依據(jù),認為PPI的上漲將傳遞到CPI),由此,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是否經(jīng)濟運行中只存在著這樣一種情形——要么“通脹”、要么“通縮”,從而,學者們需要不斷地在二者之間折騰?再次,2007-2008年間,隨著豬肉及肉制品、糧食和食用油等食品類價格的上揚(其中,豬肉及肉制品的價格上行主要由國內(nèi)因素引致,糧食和食用油價格上行主要受國際市場因素影響),中國又一次進入了CPI高漲期,由此,“治理通脹”的呼聲再次鵲起。隨著各項刺激養(yǎng)豬政策的落實和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的回落,進入2009年以后,物價大幅下行,7月份CPI為-1.8%,這應當為“治理通脹”慶賀了吧,可是一些人又再次轉(zhuǎn)向,當即提出了“治理通縮”的政策主張。在2008年的物價上漲中,并非各種消費品的價格普遍上行,在“食品”、“煙酒及用品”、“家庭設備及用品”、“醫(yī)療保健用品”和“居住”等價格上漲的同時,“衣著”、“交通和通訊工具”及“娛樂教育文化用品”等的價格處于持續(xù)降低走勢。其中,漲幅最大的是“食品”,2008年1-8月的漲幅都在兩位數(shù)。與此相比,2009年2月以后,“食品”價格呈負增長走勢(在實際生活中,豬肉及肉制品、糧食和食用油等絕對價格下降了),在此背景下,提出“治理通貨緊縮”的含義是什么呢?如果這些食品的價格不該下降,那么,為什么在2008年同期需要疾呼“治理通貨膨脹”?如果這些食品的價格應該下降,那么,提出“治理通貨緊縮”的意圖又是什么?真是不知所云。1998年以來,理論界一些人在“通脹”和“通縮”上的反復無常、莫衷一是,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面對物價變動,能否簡單地套用“通脹”或“通縮”的理論思維?換句話說,是否存在既不需要“治理通縮”也不需要“治理通脹”的物價狀態(tài)?
從1997-2007的11年間CPI分類指數(shù)的變化走勢,從中可以看到,食品類價格指數(shù)有兩次大幅上行,即2004年的9.9%和2007年的12.3%,它們是引致對應年份CPI高漲的主要成因。從具體情況看,2004年主要是糧食價格上漲,2007年以后主要是豬肉及肉制品價格上漲,這些都涉及到農(nóng)產(chǎn)品和農(nóng)民的利益。農(nóng)業(yè)是國民經(jīng)濟的基礎。在中國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也存在著支持“三農(nóng)”發(fā)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繁重而艱巨的任務,由此,提高農(nóng)民收入,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應當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予以認真解決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而且有著繼續(xù)擴大的趨勢。究其原因,農(nóng)產(chǎn)品的價值構成與工業(yè)品不同是一個主要方面。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商品價格應由C+V+M三部分構成。中國的工業(yè)品價值的確由C+V+M構成,但大部分農(nóng)產(chǎn)品卻只由C+V構成。由于在農(nóng)產(chǎn)品中缺乏M,所以,資本進入農(nóng)業(yè)的傾向大大減弱,金融服務于農(nóng)業(yè)的程度也明顯不足。盡管如此,對農(nóng)民來說,只要能夠保證V的獲得,也還有種糧養(yǎng)豬的積極性。但是,糧價在1996年達到了高點(84.23元/100斤)以后就一路下落,到2000年降至谷底(49.39元)/100斤,跌幅深達41.36%。在此背景下,隨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的價格上漲,農(nóng)產(chǎn)品中C部分加大,V的獲得更加缺乏保障,在此背景下,盡管各地方政府采取了種種措施力保糧食生產(chǎn),但糧食種植面積還是從1998年的113787公頃減少到2003年的99410公頃(降幅達到12.63%),由此,引致了糧食的年產(chǎn)量從1998年的51229.5萬噸減少到2003年的37428.7萬噸(降幅達到26.94%)。這是2003年底至2004年物價大幅上漲的基本成因。支持這一物價上漲,意味著讓農(nóng)民多少能夠從糧食及其他農(nóng)產(chǎn)品中獲得一些收入,以維系V的應有水平,激勵他們的種糧積極性。但所謂的“治理通脹”則要求抑制糧食及其他農(nóng)產(chǎn)品的價格上漲,使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繼續(xù)處于受挫狀態(tài)。顯然,從實踐面情況看,此時提出“治理通脹”是不合時宜的。實踐中的政策選擇是,在放棄動用國家儲備糧打壓糧價、讓市場機制推進糧價回升的同時,財政部門對種糧農(nóng)民進行了按照耕種面積的“直補”,從而刺激了農(nóng)民種糧積極性,使得2004年扭轉(zhuǎn)了持續(xù)4年的糧食減收走勢,穩(wěn)定了糧食價格,促使CPI增長率下行。
2007年初發(fā)生了新一輪的物價高漲,它主要由豬肉及肉制品所引致。與2006年相比,2007年肉豬出欄減少了4699萬頭(即下降了7.68%),豬肉產(chǎn)量減少了362.7萬噸(即下降了7.80%)。豬肉產(chǎn)量減少的成因主要在于養(yǎng)豬成本的上升,其中包括飼料價格升高、防疫(如藍耳病等)成本提高和規(guī)模化養(yǎng)豬的設施成本上升等。由于原先豬肉的價格水平無力消化這些成本上升引致的養(yǎng)豬虧損,所以,一些農(nóng)民不愿繼續(xù)養(yǎng)豬,由此,導致豬肉供不應求,豬肉價格隨之走高并推動了CPI上行。但一些學者無視這一現(xiàn)實現(xiàn)象,再次提出了“治理通脹”的政策主張,好在實際操作中,有關政府部門采取了財政補貼,其中包括無償防治藍耳病、給每只母豬以一定數(shù)額的財政資助等,由此,在2008年下半年,生豬存欄量大幅增加,生豬價格從10元/斤左右直線下落到6元/斤左右。豬肉及肉制品價格的下落,促成了CPI下行。2008年1-8月,食品類價格指數(shù)上漲率均在2位數(shù)(其中最高的是4月份22.1%),但到2009年2月以后,隨著豬肉價格絕對水平的降低,CPI也就呈負增長走勢。在此背景下,再次提出“治理通貨緊縮”的實踐含義是什么?是預期讓豬肉及肉制品再陷入短缺境地從而價格繼續(xù)走高,還是預期使食品類中的其他產(chǎn)品(如糧食等)價格走高,以便在CPI上行中又一次炒作“治理通脹”?
從實踐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論是“治理通脹”還是“治理通縮”都無助于解決1998年以來中國實踐中發(fā)生的CPI增長率變動,要真正解決問題,還需要針對物價變動的具體成因,分別選擇不同的政策措施。
最后,從政策層面看,既然將物價變動簡單地定義為貨幣政策松緊的現(xiàn)象,既然央行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是保持幣值穩(wěn)定(而物價變動意味著幣值變動),所以,在物價變動中,主張調(diào)整貨幣政策松緊程度的呼聲不絕于耳。從歷史線索看,(1)在所謂“通縮”的背景下,1996-2002的7年間,央行先后8次下調(diào)了存貸款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下落到1.98%、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落到5.31%,其力度不能說不大。下調(diào)存款利率的一個重要意圖是,希望城鄉(xiāng)居民少存款多消費,但結果是,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1995年底的2.97萬億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8.69萬億元(原先每年新增儲蓄存款6000億元左右,但2000年之后,每年新增儲蓄存款在1萬億元左右),另一方面,這段時間內(nèi)的CPI走勢并沒有發(fā)生實質(zhì)性改變。(2)在2003-2004年的所謂“治理通貨膨脹”過程中,央行于2003年9月和2004年4月分別兩次提高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共1.5個百分點)、于2004年10月提高存貸款利率(1年期存貸款利率分別上調(diào)0.27個百分點),但這些措施對緩解糧食產(chǎn)量的下降并無多少正面效應,相反的,它引發(fā)了其他一系列問題的產(chǎn)生。 2004年5月以后,民營經(jīng)濟發(fā)展陷入困難境地、證券公司大幅虧損(以致10月份以后,一大批證券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由此,拉開了證券公司破產(chǎn)整頓的序幕)等等,與此時緊縮的貨幣政策不無關系。(3)2007-2008年間CPI高增長期間,央行先后16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9%上升到17.5%)、6次提高存貸款利率,但并沒有因此遏制住CPI不斷上行的勢頭;2008年9月以后的3個多月時間內(nèi),連續(xù)4次下調(diào)法定存款準備金率、5次下調(diào)存貸款利率(使1年期存款利率回到了2004年10月底的水平,1年期貸款利率回到了2002年2月的水平),但CPI下行的走勢并沒有因此而改變。在這些調(diào)整中,一系列負面效應隨之而來:其一,對養(yǎng)豬戶而言,提高利率無助于豬肉及肉制品價格進一步上升,但貸款利率的上升將使養(yǎng)豬專業(yè)戶的成本(包括由貸款利率上行引致的飼料價格上升)增加,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財政補貼的效能。其二,在不斷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過程中,對中小存貸款金融機構來說,由于缺乏外匯資產(chǎn),只能上繳人民幣資金,由此,陷入可貸資金緊張狀態(tài),這進一步引致了中小企業(yè)貸款的縮減和貸款利率上行,加重了中小企業(yè)融資的困難。其三,干擾了貨幣政策目標的實施。其四,影響了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進程。2004年10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fā)布了《關于調(diào)整人民幣基準利率的通知》,強調(diào)貸款利率以基準利率為下線,上限全部放開,由各家存貸款金融機構“根據(jù)自身經(jīng)營狀況、資金成本和企業(yè)風險程度等因素合理確定存貸款利率”,這意味著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將邁出實質(zhì)性步伐。在商業(yè)銀行體系內(nèi)資金過剩背景下,貸款利率本來有著下行要求(至少說,持續(xù)上行是相當困難的),但在“治理通脹”過程中,強制性地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由此,影響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的應有進程。
中國有句俗語:殺雞焉用牛刀。1998年以來中國物價變動的具體成因在各個時期是不一樣的,理應選擇“具體問題具體解決”的研討思路和政策取向,但將這些物價變動冠之以“通脹”或“通縮”并由此引致運用貨幣政策,以需求總量政策來解決某種農(nóng)產(chǎn)品供不應求(或提高農(nóng)民生產(chǎn)這種農(nóng)產(chǎn)品的積極性)問題,只怕是“雞未能殺死”卻“傷了自己”。
走出“通脹”或“通縮”的思維誤區(qū)
物價走勢是判斷宏觀經(jīng)濟走勢的一個重要指標。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經(jīng)濟運行走勢,不僅對中國的未來發(fā)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球經(jīng)濟的復蘇也是舉足輕重的。2009年1-7月,中國經(jīng)濟運行撲朔迷離,新增貸款規(guī)模、固定資產(chǎn)投資規(guī)模等創(chuàng)下了歷史新高,工業(yè)增加值、制造業(yè)采購經(jīng)理指數(shù)(PMI)和發(fā)電量緩慢回升,股價、房價上行趨勢明顯,物價、出口增長率繼續(xù)維持負增長,GDP在第二季度達到7.9%的基礎上還將繼續(xù)上行。從2009年的后期看,新增貸款規(guī)模、固定資產(chǎn)投資規(guī)模的全年高增長已成定局,工業(yè)增加值、制造業(yè)采購經(jīng)理指數(shù)(PMI)、發(fā)電量、股價、房價等將繼續(xù)上行,物價上漲率、出口增長率可能轉(zhuǎn)負為正,第四季度的GDP可能達到10%左右,照此慣性運行,2010年上半年的中國經(jīng)濟將在高位運行,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經(jīng)濟是否又進入了一個類似于2007年的“過熱”區(qū)間?與此對應,是否需要再來一次宏觀經(jīng)濟緊縮? 在做這一判斷中,對物價變動狀況的認定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雖然在新增貸款規(guī)模和固定資產(chǎn)投資規(guī)模等高增長而CPI負增長的背景下,有人強調(diào)要“治理通縮”,有人則強調(diào)要“防止通脹”,這些爭論還難有定數(shù),可是一旦CPI轉(zhuǎn)向正增長,“治理通脹”的呼聲就將占據(jù)上風。
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是,在產(chǎn)能過剩比較嚴重的格局中,中國目前并不具備通脹的現(xiàn)實條件,同時,按照2008年物價上漲的翹尾因素分析,2009年的物價應當呈負增長走勢,但是,在《政府工作報告》所列的2009年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中,居民消費價格(CPI)漲幅被界定在4%左右。如此高的CPI目標,是計算缺乏科學性,還是已有一些價格調(diào)整的預案?從該報告的“2009年主要任務”中可以看到:“推進資源性產(chǎn)品價格改革。繼續(xù)深化電價改革,逐步完善上網(wǎng)電價、輸配電價和銷售電價形成機制,適時理順煤電價格關系。積極推進水價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農(nóng)業(yè)用水價格,完善水資源費征收管理體制。加快建立健全礦產(chǎn)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tài)補償機制,積極開展排污權交易試點。”這意味著,在2009年間,隨著國民經(jīng)濟增長態(tài)勢轉(zhuǎn)好,各項經(jīng)濟指標比較理想時,可能啟動水、電、燃氣等方面的價格改革,這將推動CPI呈正增長走勢。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這種由價格調(diào)整所引致的CPI正增長是否也屬“通脹”,需要用從緊的貨幣政策措施予以抑制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則不僅與政府的價格調(diào)整政策相矛盾,而且將引致更為嚴重的宏觀經(jīng)濟緊縮后果。
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和今后的進一步發(fā)展中可以看到,物價變動是由多種成因所致,其中大多數(shù)與貨幣政策的松緊基本無關,因此,既不能用“通脹”或“通縮”冠之,也不應對CPI變動簡單地采取對應的貨幣政策。只有那些因貨幣發(fā)行過多引致的物價上漲或因貨幣發(fā)行過少引致的物價下降,才可冠之以“通脹”或“通縮”,選擇對應的貨幣政策實施影響。
必須認識到一個重要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在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中,農(nóng)產(chǎn)品、資源類產(chǎn)品(包括礦產(chǎn)品、水、電和燃氣等)的價格上行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趨勢。這既由資源的稀缺性所決定,也由這些產(chǎn)品生產(chǎn)的成本(包括環(huán)保成本)上升所決定。在此背景下,由這些產(chǎn)品價格上行所引致的物價上漲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鑒于中國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剪刀差,要真正維護農(nóng)民利益、推進“三農(nóng)”發(fā)展、激勵資本向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的上漲也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宏觀調(diào)控的目標不在于抑制這些產(chǎn)品的價格上漲(從而抑制由此引致的CPI上行),而在于熨平這種價格上漲走勢,以防價格上漲過快而影響到經(jīng)濟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從這個角度上看,問題不在于“治理”,而在于“熨平”。毫無疑問,在“熨平”這些產(chǎn)品價格上漲過程中,還需運用財政政策,在一定時期內(nèi)該補貼的還要補貼,但總的取向不應是“補貼”;應當讓農(nóng)民獲得按照市場機制所能夠獲得的收入,在此基礎上,再討論財政補貼問題。否則,本末倒置,將引致更加嚴重的負面后果。
面對由貨幣發(fā)行量引致的物價上漲,貨幣政策的松緊確有其功效。但面對不是由貨幣發(fā)行量引致的物價上漲,貨幣政策的松緊非但沒有功效而且有著諸多負面效應。由此來看,將貨幣政策目標界定在“保持貨幣幣值的穩(wěn)定”上是值得重新探討的。其一,貨幣政策沒有在任何物價變動條件下都保持幣值穩(wěn)定的功能,因此,做不到、也達不到這一目標。其二,將這一目標界定為央行工作的主要目標,容易使央行在面對物價變動中處于被動境地,不得不頻繁地出臺相關貨幣政策調(diào)整措施(以擺脫被動處境),而這些貨幣政策舉措可能不僅無的放矢,而且將引致不良后果。其三,央行雖是貨幣政策的調(diào)控主體,但也是維護金融運行穩(wěn)定的主要部門。“保持貨幣幣值的穩(wěn)定”主要目的還在于維護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穩(wěn)定。在防范此輪全球金融危機再度發(fā)生過程中,西方主要國家已將維護金融穩(wěn)定提高到至少不低于貨幣政策的程度。在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金融穩(wěn)定的重要性也將日益凸顯,為此,與其將央行的主要工作目標界定為“保持貨幣幣值的穩(wěn)定”,不如將其界定為“保持金融運行秩序的穩(wěn)定”。這也有利于避免“一旦CPI發(fā)生變動,就找央行(或貨幣政策)”的傾向繼續(xù)發(fā)生。
CPI漲跌和物價變動并不對等,其中一個重要差別在于CPI中各種產(chǎn)品價格的權重設置。在中國的CPI中,食品類所占權重達到1/3,這在推進溫飽型小康過程中是合適的。但如今,溫飽型小康已經(jīng)基本實現(xiàn),在推進全面小康過程中繼續(xù)采取這種權重計算方法,就容易產(chǎn)生負面影響。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是,一旦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上漲,CPI隨之反應,而根據(jù)“通脹”思維所采取的貨幣政策直接要求抑制農(nóng)產(chǎn)品的價格上行。這不利于維護農(nóng)民的利益,也不利于理順價格體系。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是指各種物價(主要是工業(yè)制成品)近乎普遍地持續(xù)(一般以6個月以上為度量標準)上漲或下跌的走勢。據(jù)此,CPI的權重構成調(diào)整可以選擇兩種方法:一是計算核心CPI,以此為度量是否通脹或通縮的指標。在核心CPI中,不列入食品類,由此,它只反映工業(yè)制成品的價格變動趨勢,更緊密地反映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經(jīng)濟運行態(tài)勢。二是降低食品類在CPI中的權重,從目前的1/3降低到與美國、印度等相近的水平(即10%左右),以減輕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變動對CPI的影響程度。兩種方法中,前者為好;當然,也可兩種方法都選用,但以前一種方法為主。

 在線客服
在線客服
 企業(yè)微信
企業(yè)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