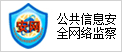從汽車組裝到鍵鼠制造,機器人正在入侵越來越多的中國工廠。
深圳北部的坪山,一個無塵表面處理車間的外走廊,鄧邱偉隔著玻璃,凝視著兩個橙色的六軸工業機器人的“親吻”。如同櫥窗里的表演,它們高低旋轉著,不斷把塑膠開關抓取到空中,將薄薄的開關貼紙貼上,又把開關放到設計好的料盒上。
“這是我們廠里(機器人做出的)最漂亮的動作。”鄧邱偉回過頭,對本刊記者贊美著。
然后,他的話題重回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總監的角色:“單是這兩個機器人的‘親吻’,就已經幫我節省了很多工人。”
鄧邱偉今年30歲,他的直接上司——雷柏董事長兼總經理曾浩剛過40歲。作為珠三角成百上千家鍵鼠工廠的一員,他們的工廠并不那么傳統,因為它不用工人的數目來展現自己的制造能力。
雷柏2011年有大約3000個產業工人,而到記者上月訪問時,這個數字已經“銳減”到不足1000人,產能卻“至少增加了三倍”。
這種情景在2011年還僅存于想象中——“老板(曾浩)說,雷柏以后的工廠就是1000個人。我想,當時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覺得他是瘋子。”鄧邱偉形容。
當勞動力成本的爬升令中國的制造工廠們感到苦惱時,雷柏徹底把機器人和自動化設備變成了工廠里的主角。雷柏生產的、提供給人們手指敲擊和挪移的鼠標、鍵盤,已不再依賴工人們的雙手來制造,工人數字的銳減甚至震蕩了雷柏的管理架構。
曾浩的目標很徹底:讓雷柏的工廠變成一個看不見幾個工人的地方,就像現代的汽車裝配車間那樣。在成本壓力日增的電腦周邊設備行業里,這種大變動,看上去如同“強行超車”般冒險,卻又是應對競爭的必然。
自動化實驗
“我們想擺脫對工人的依賴”
現在,在雷柏的車間里,偶爾可見“穿越”的場景——用以過渡的,臨時組織的人手裝配線,夾在轟隆開動的自動化生產線之間。前者就像人手生產的歷史演示,后者則由各種機械手和傳送設備配合著運轉,機器人的橙色晃動其中,甚是搶眼。
變化猶如一夜間發生。2009年,當鄧邱偉跳槽到雷柏時,曾浩告訴他,目前工廠是整個公司里面最弱的部分。“即便到現在,整個珠三角的同類工廠都是以人手作業的。我們想擺脫對工人的依賴。”鄧邱偉說。
早年,雷柏的工廠是珠三角眾多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r,原始設計商)工廠的普通一分子,以工人數字和廠房規模來宣揚自己的制造實力。在那個用“人多”招徠大客戶的年代,包括雷柏內部的宣傳,也用工人數目的增長來描述公司發展的速度。
曾浩喜歡穿牛仔褲和白球鞋,他還有一部法拉利,不時到珠海的賽車場飆車。在研發方面,曾浩已經把無線鍵鼠業帶入了2.4G的軌道。在看似波瀾不驚的鍵鼠行業,曾浩也希望領跑品牌和生產領域。
2002年,曾浩創立了“雷柏”品牌,開始在海內外擴張銷售。幾年來,雷柏的競爭壓力迅速增大,國際同行和山寨廠“夾擊”著這個無線鍵鼠領域的新丁。“(在生產中發掘潛力)這是被逼出來的。”10年前與曾浩一起創立雷柏的李錚說,“你必須在成本上保持優勢。”
按照雷柏高層的說法,他們關注自動化的原因,跟其他工廠一樣“因勢所迫”。從2005年開始,雷柏和其他珠三角的工廠一樣,開始遇到用工荒,以及“工人說走就走”等管理問題,這讓機器在生產線上得到了機會。
“在PCB板上插嵌精細的元件,這種動作很勞累。因為手要不停地動,做得好的話,更需要一個月以上的經驗積累。”在雷柏車間僅剩的、工人們默默重復手工插電動作的生產線前,27歲的班組長余建輝描述著工人們的難處,“如果加班,工人們的情緒更不好應對。”
“人海”生產線上還有其他不穩定因素。2002年,當曾浩拿著設計方案,在深圳從事鼠標生產時,他已經發現,由一對對人手組成的生產線,具備應對不同代工客戶的靈活性,但代工廠們制造的產品品質卻“非常不穩定”。
從2007年開始,雷柏工廠成立了自動化小組,開始了減少對產業工人依賴的嘗試。第一次大實驗戲劇性地發生在次年:曾浩向海外ODM客戶展示了還沒完成研發的自動化生產設備,并成功取得了大額鍵盤訂單;客戶貨期的逼近,逼著自動化小組起早摸黑地敲打出一條業內首例的自動化鍵盤生產線。
這條生產線現在仍在雷柏的一個隔音房里作業。它看起來略顯粗糙,運行時會發出轟隆的響聲,放出大量的粉塵,但它能自動完成打螺絲、安鍵帽、打油等工序,在當年甚為罕見。更重要的是,它“花費30萬,解決了鍵盤生產線上工人一百零幾個插鍵帽的動作,把線上的工人從60人減到24人”。
機器人進駐
價錢下降三分之一時,機器人立即成為雷柏工廠的新寵。
引入機器人以前,雷柏的自動化小組一直是個挨罵多于被贊賞的部門。“自動化設備缺乏穩定性,通常研發成功一套生產設備,換一個產品這設備就變得沒用了,在倉庫里折舊了。”鄧邱偉說。
硬邦邦的、自制的自動化機械有著天然的硬傷:只擅長解決通用產品或大批量產品的制造。相應之下,雷柏曾經為眾多ODM客戶服務,工廠每天都得調整生產線,以工人為主(尤其是經驗豐富的熟手工人們)

 在線客服
在線客服
 企業微信
企業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