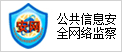多哈談判之前,世界銀行和國際能源署已經警告如果仍不采取大規模減排,全球將面臨升溫4-6攝氏度的風險,而目前國際社會公認的控制目標僅僅是2攝氏度。多哈談判決定著后京都時代全球氣候制度的新格局,與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相比,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不變的是美國依然是阻礙氣候談判的關鍵因素。
1997年美國最終決定簽署《京都議定書》,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盟與美國的相互讓步,以及布萊爾政府的大力周旋。京都談判的最后幾天,美國同意減排目標設定為7%,歐盟同意將溫室氣體種類從3種擴大到6種,并允許使用靈活機制和碳匯,而事實上碳匯的使用正好相當于美國7%的減排目標。《京都議定書》為未來的全球氣候制度建立了框架,但之后談判再次步入僵局。在2000年的海牙會議臨近結束時,時任的英國首相布萊爾與美國總統克林頓進行了數個小時的通話,達成了一份內部協議,但最終由于部分歐盟國家的反對而失敗。錯過了此次機會之后,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全球氣候談判進入了“失去美國”的10年。
2008年競選成功的奧巴馬政府曾經給氣候談判帶來希望,而金融危機也的確給奧巴馬新政帶來了歷史性機遇,不過他們最終還是錯過了。《2009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以及《2010美國電力法》最終都倒在通往參議院的道路上。以共和黨為核心的強大利益集團,以及醫改法案大山最終讓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放棄氣候變化這個“燙手的山芋”和“打飛的子彈”,轉而主攻以國家安全為核心,以“華爾街+硅谷”模式為主導的新能源經濟戰略。事實上,從2010年開始,我們已經很難聽到來自奧巴馬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強勢言論。美國依然固執地執行單邊主義策略,而歐洲則深陷經濟危機,有心無力。
但這并不代表處于“深度死鎖”狀態的氣候談判全無生機。2007年《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談判啟動以來,全球氣候格局已發生了深刻變化。最大的變化來自于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強有力的挑戰。在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簽訂前,正是歐盟成功說服美國、日本等,將這一原則寫入UNFCCC,成為氣候談判最重要的南北共識。但隨著金磚四國的迅速崛起,以及歐美經濟的疲軟,歐盟在這方面的立場已經開始明顯動搖。特別是中國從2009年之后被國際輿論一致認定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國和溫室氣體排放國,是否繼續對中國、印度等經濟大國采用這樣的原則,成為氣候談判的核心議題。第二個變化則是全球目標的形成。如果回到10年前,誰若是說要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到2攝氏度以內,人們一定會以為他是瘋子或者NGO成員,并逐出氣候談判的會場。而最近幾年,隨著科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越來越深入,主流觀點早已度過了辯論氣候變化真偽的階段,將重點轉到目標設定和經濟政策實施上。
多哈會議毫無疑問將在這兩個大的方向中繼續前進,而另外一個很有可能帶來重大變化的因素則來自于美國的頁巖氣革命。阻礙美國氣候談判的關鍵力量一直是傳統能源集團,迫使其無法做出實質性的減排承諾。美國的人均排放和單位GDP排放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美國模式成為高排放的代表。而頁巖氣產業的快速發展讓美國一下子具備了巨大的減排空間,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美國在過去5年內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4.5億噸,預計到2035年能夠實現能源自給自足。頁巖氣革命改變了美國的能源結構和發展藍圖,這使得奧巴馬政府在多哈談判中有了更多的周旋空間。
另一方面,中國近幾年的談判策略也開始變得更加靈活,正在尋求適當的途徑體現大國責任。中美之間是否能夠達成妥協將成為此次談判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但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美國擁有了更加靈活的談判策略,那么中美之間最近幾年形成的默契也很可能隨之破裂,中國面臨的談判形勢或將變得更加復雜和具有挑戰性。

 在線客服
在線客服
 企業微信
企業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