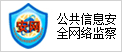核心提示:
在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上,經濟學家似乎比政府著急,不少學者講起經濟復蘇來憂大于喜,而講起“退出”來卻比誰都更迫不及待。在他們看來,目前國內可以看到的經濟復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結果。如果這樣的貨幣政策再持續下去,三五年之后中國銀行體系將出現大量壞賬。換言之,人們所喜聞樂見的經濟復蘇,在那些經濟學者看來,是通貨膨脹或資產價格泡沫。有經濟學家更是危言聳聽,說如果不能未雨綢繆,盡早退出,勢將重蹈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覆轍。
只要稍稍找出此類預言的邏輯混亂之處,就不難明白,這些杞人憂天的預言,根本就不足采信。
首先,如果沒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有為,不要說美國,就是中國也不可能出現好于全世界經濟復蘇水平的GDP增長趨勢。盡管此次金融危機的一些深層次潛在危機也許還尚未充分表現出來,但是,如果沒有積極的救市措施,岌岌可危的美國金融和經濟局勢將是不可想象的。這一點,誰也不能否定。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4萬億投資,沒有差不多8萬億的信貸擴張,中國經濟也不可能在出口受阻的情況下依然保持8%以上的增長率。把原本就已存在的結構性產業過剩說成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并以此而否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太不實事求是。把經濟復蘇的初步實現說得比走不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可怕,那就更是不可思議的荒謬之論了。
其次,理論上的通脹預期和現實的通脹是兩回事。盡管不能不看到,大量的貨幣發行必然會帶來通脹的壓力,即使目前在消費品方面還沒有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也并不意味著未來就沒有壓力,更不意味著我國沒有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但至少在眼下,通縮而不是通脹,才是真正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中國特殊國情。在我國的國民消費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從科學發展角度來說,要轉變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模式,就必須使得消費成為國民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拉動力,千方百計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在這方面,政策應成為積極引導消費,走出現實通縮的向導,而不能一味地充當影子通脹的尾巴。
此外,對于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資產價格泡沫,也需要有個辯證的態度。美國的那位格林斯潘,雖曾被稱為“反通脹斗士”,但對于泡沫卻一直有著他的獨特看法。他不僅認為人類還沒有找到對付泡沫的靈丹妙藥,而且還主張不應主動刺破泡沫,而只需要為限制泡沫破滅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做好充分準備,格老因此而又被視為“泡沫先生”。 筆者在此決無任何為格老“泡沫論”辯護的意思,不過,他所指出的主動刺破泡沫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在日本倒是有過驗證的。可惜,現在世人談論日本教訓時,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問題。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日本經濟泡沫的根源。野村證券經濟學家木下智夫則認為,一些轉型政策,比如急速調整日元匯率、深化債券市場以及利率自由化等,才是泡沫破裂背后的基本原因。日本盛極而衰的種子,其實在1985年廣場協議決定日元升值的那一刻就埋下了。正所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伴隨著日元的大幅波動,日本樓市先暴漲,后暴跌,最終令日本經濟滑入“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由此可見,刺破泡沫也許是件很容易的事,而限制和彌補泡沫破滅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卻很不容易。
歷史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現下的中國不僅被一些經濟學家認定正在重蹈日本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泡沫極度膨脹的覆轍,而且他們所設計的所謂“退出戰略”的切入點,無巧不巧地正好也是人民幣匯率。央行最近關于匯率形成機制的表述出現了微妙變化,“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結合國際資本流動和主要貨幣走勢變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提法,被廣泛理解為人民幣將主動升值的暗示。如果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穩定作為用于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的退出,那么,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等其他的非常措施,豈不一樣更需要有周全的退出策略?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態勢很不平衡,我國經濟回穩的趨勢雖然正在逐漸明朗,但不僅外部需求不斷萎縮的局面尚未有根本性改觀,而且深層次問題也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操之過急的退出戰略,不但很不合時宜,而且也很容易引發新矛盾、新問題。中國經濟好比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車,就是需要轉向也得轉個大彎,而不能“急轉彎”,急退就更不要說了。
稍早時候的APEC財長會議提出,在目前復蘇基礎尚不穩固的情況下,要避免過早地退出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溫家寶總理最近也表示,中國將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顯然,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回歸常態的過程,必然是而且也只能是一個理性的調整和緩慢的轉向過程。
只要稍稍找出此類預言的邏輯混亂之處,就不難明白,這些杞人憂天的預言,根本就不足采信。
首先,如果沒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有為,不要說美國,就是中國也不可能出現好于全世界經濟復蘇水平的GDP增長趨勢。盡管此次金融危機的一些深層次潛在危機也許還尚未充分表現出來,但是,如果沒有積極的救市措施,岌岌可危的美國金融和經濟局勢將是不可想象的。這一點,誰也不能否定。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4萬億投資,沒有差不多8萬億的信貸擴張,中國經濟也不可能在出口受阻的情況下依然保持8%以上的增長率。把原本就已存在的結構性產業過剩說成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并以此而否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太不實事求是。把經濟復蘇的初步實現說得比走不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還可怕,那就更是不可思議的荒謬之論了。
其次,理論上的通脹預期和現實的通脹是兩回事。盡管不能不看到,大量的貨幣發行必然會帶來通脹的壓力,即使目前在消費品方面還沒有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也并不意味著未來就沒有壓力,更不意味著我國沒有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但至少在眼下,通縮而不是通脹,才是真正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中國特殊國情。在我國的國民消費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從科學發展角度來說,要轉變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模式,就必須使得消費成為國民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拉動力,千方百計拓展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在這方面,政策應成為積極引導消費,走出現實通縮的向導,而不能一味地充當影子通脹的尾巴。
此外,對于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資產價格泡沫,也需要有個辯證的態度。美國的那位格林斯潘,雖曾被稱為“反通脹斗士”,但對于泡沫卻一直有著他的獨特看法。他不僅認為人類還沒有找到對付泡沫的靈丹妙藥,而且還主張不應主動刺破泡沫,而只需要為限制泡沫破滅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做好充分準備,格老因此而又被視為“泡沫先生”。 筆者在此決無任何為格老“泡沫論”辯護的意思,不過,他所指出的主動刺破泡沫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在日本倒是有過驗證的。可惜,現在世人談論日本教訓時,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問題。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日本經濟泡沫的根源。野村證券經濟學家木下智夫則認為,一些轉型政策,比如急速調整日元匯率、深化債券市場以及利率自由化等,才是泡沫破裂背后的基本原因。日本盛極而衰的種子,其實在1985年廣場協議決定日元升值的那一刻就埋下了。正所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伴隨著日元的大幅波動,日本樓市先暴漲,后暴跌,最終令日本經濟滑入“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由此可見,刺破泡沫也許是件很容易的事,而限制和彌補泡沫破滅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卻很不容易。
歷史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現下的中國不僅被一些經濟學家認定正在重蹈日本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泡沫極度膨脹的覆轍,而且他們所設計的所謂“退出戰略”的切入點,無巧不巧地正好也是人民幣匯率。央行最近關于匯率形成機制的表述出現了微妙變化,“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結合國際資本流動和主要貨幣走勢變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提法,被廣泛理解為人民幣將主動升值的暗示。如果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穩定作為用于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的退出,那么,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等其他的非常措施,豈不一樣更需要有周全的退出策略?
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態勢很不平衡,我國經濟回穩的趨勢雖然正在逐漸明朗,但不僅外部需求不斷萎縮的局面尚未有根本性改觀,而且深層次問題也還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操之過急的退出戰略,不但很不合時宜,而且也很容易引發新矛盾、新問題。中國經濟好比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車,就是需要轉向也得轉個大彎,而不能“急轉彎”,急退就更不要說了。
稍早時候的APEC財長會議提出,在目前復蘇基礎尚不穩固的情況下,要避免過早地退出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溫家寶總理最近也表示,中國將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顯然,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回歸常態的過程,必然是而且也只能是一個理性的調整和緩慢的轉向過程。

 在線客服
在線客服
 企業微信
企業微信